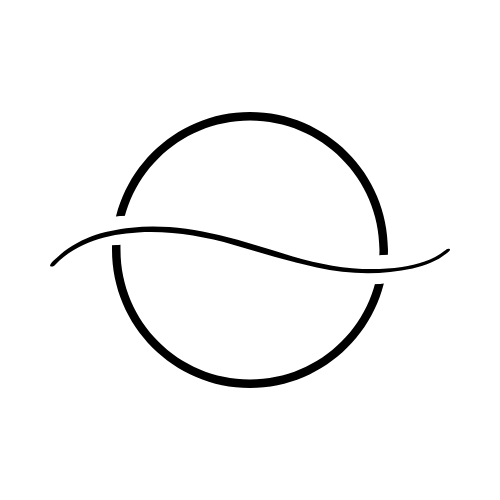人当何为
What To Do|By Paul Graham

原文:What To Do
保罗·格雷厄姆是一位兼具黑客精神与思想锋芒的作家、程序员、创业导师。他是知名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的联合创始人,这个机构曾孕育出 Airbnb、Dropbox、Stripe 等硅谷传奇公司。更早之前,他是一位 Lisp 编程语言的专家,也创办过被 Yahoo 收购的 Viaweb。
但比起“创投教父”的身份,许多读者更熟知他那一篇篇洞察人性与时代变迁的随笔。在这些文字中,格雷厄姆既以程序员的理性解构社会机制,又以作家的敏锐洞察技术如何悄然改变我们的行为、选择。
发表于2025年3月
“人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乍听之下有点奇怪,但其实既不无意义,也并非无法回答。这正是孩子在学会“别问太大问题”之前常会提出的问题。我自己也是在研究别的事时偶然撞上它的。但既然撞上了,我觉得自己至少应该试着回答一下。
所以,人该做些什么?应该帮助他人,关心世界。这两个答案显而易见。但除此之外呢?当我继续追问,脑中浮现出的答案是:创造美好的新事物。
我无法证明人就该这么做,就像我无法证明人就该帮助别人或关心世界一样。我们讨论的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但我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原则是有意义的:人类最令人惊叹的能力是思考——这也许是宇宙间最了不起的能力。而最优质的思考,或者说最能证明你真的动过脑子的方式,就是创造出美好的新事物。
这里的“新事物”,我指的是广义上的。牛顿的物理学体系就是一种美好的新事物。事实上,这个原则最初的版本是“提出优质的新想法”。但后来我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够广泛:它没能包含艺术或音乐的创作,除非你把它们也勉强归为“新想法”。虽然艺术和音乐确实可能包含新的思想,但它们远不止于此——除非你把“想法”这个词拉扯得无限泛滥,以至于连神经系统里的一切都算进去。
即便是对那些你确实有意识地产生的想法,我也更喜欢“创造美好的新事物”这种表述。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描述高水平的思考,比如“发现”或者“比他人更深入地理解某个事物”。但如果你无法构建一个模型,无法把它写出来,你真的理解它了吗?其实,尝试表达你所理解的,不只是检验理解的手段,更是深化理解的过程。
我之所以偏爱“创造”这个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天然带有建设性的偏向。它鼓励我们更倾向于那些能“做出点什么”的想法,而不是那些只对别人的作品提出批评的想法。后者当然也是“想法”,有时也很有价值,但人很容易被自己骗了,以为它们比实际更重要。批评听起来高深,而创作在起步阶段往往笨拙;但正是这种笨拙的起步,才是最稀缺、最珍贵的。
那“新”是否是必要的?我认为是的。在科学中,这毫无疑问。如果你照搬别人的论文还署上自己名字,那不仅不令人佩服,反而会让人觉得你不诚实。在艺术中也是如此。一幅优秀画作的复制品可以令人愉悦,但它并不像原作那样令人惊叹。这也意味着,无论你做得多熟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其实也只是换种方式在“抄袭”。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应该”跟我们通常说的“应该”有所不同。帮助他人、关心世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创造美好的新事物,则是一种实现自我潜能的方式。历史上关于“该如何生活”的规则,往往是这两种“应该”的混合体——只不过一般更强调前者而非后者。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无论你问的是西塞罗还是孔子,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做一个智慧、勇敢、诚实、节制、公正的人,恪守传统,服务公共利益。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在世界某些角落,这个答案换成了“侍奉上帝”,但实际上,人们仍然认为具备上述那些品质是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对此恐怕也会点头称是。
但在这些答案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关心世界”或“创造新事物”的影子,而这多少有些令人担忧——因为这个问题本应是一个跨越时代的永恒之问,答案不该变得太多才对。
我倒不太担心传统答案没提“关心世界”。毕竟,只有当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把世界搞砸之后,才真正开始关心它。但“创造美好的新事物”呢?如果这真的重要,那传统的智慧为何从未提及?
问题在于:那些传统答案,其实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应当去做什么”。古代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他们的生活道路早就被画好:他们是地主阶层,同时也是政治阶层,并不需要在研究物理和写小说之间做选择。他们的“正业”就是管理庄园、参与政务、在必要时上战场。偶尔也可以在闲暇时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但理想情况下最好是“没有闲暇”。西塞罗的《论义务》可谓古代关于“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代表作之一,而他自己也在书中明说,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风波将他逐出政坛,他压根不会有时间写这本书。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人在做我们今天称之为“原创性工作”的事,他们往往也受到一定的敬重。但他们并不被视为楷模。阿基米德知道自己是第一个证明球体体积为其外切圆柱体积三分之二的人,他对此深感自豪。但你不会在古代文献中看到有人鼓励读者去效仿阿基米德。他们更把他当成一个异类奇才,而非值得追随的榜样。
而如今,我们中有更多人可以像阿基米德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类工作上。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榜样——和一批其他同样“异类”的人一样。这些人虽然在当时并未被归为一类,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在社会阶层的横切面上,开辟出了一条“创造之路”。
那么,什么样的新事物才算“美好”?这个问题我宁愿留给创造者自己去回答。划定标准其实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因为很多新型工作在初期往往并不受重视。雷蒙德·钱德勒写的小说,按当时的标准就是彻头彻尾的“通俗读物”,如今却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这个模式太常见了,以至于几乎可以反过来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你对某种不被主流看好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且能说清楚别人忽略了它的哪些价值,那这不光是“可以去做”的事,甚至是你应当主动去做的事。
我不愿意设定标准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它们。那些真正能创造出好东西的人,压根用不着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诚实。
所以,这就是我对于“人生应守的原则”的一个猜测:关心他人和世界,创造美好的新事物。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比例践行这两个目标。有的人会专注于照顾他人,有的人则几乎全心投入于创造。但即便你属于后者,至少也应该确保自己创造的新事物不会对人或世界造成伤害。而如果你更进一步,努力创造能带来积极影响的东西,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其实得到了更大的回报。你确实会受到更多限制,但你做事的能量也会因此更充沛。
当然,若你真的创造出某种了不起的东西,往往也会在无意间帮助到他人或世界。牛顿靠的是好奇心与野心驱动,他并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而做研究的——但他的研究成果却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而这并非特例,几乎已成常态。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凡之物,那大可不必犹豫,去做就是了。
注释
[1]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三条原则都视作同一种“应该”,比如说:人有责任好好地活着——比如像一些基督徒说的那样,人有责任善用上帝赐予的天赋。但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是为了逃避宗教的严格要求而生出的“巧辩之词”:比如,你不去祷告或行善,而是花时间研究数学,也可以说自己是在履行对上帝的责任,因为你若不用这个天赋,就是在拒绝祂的恩赐。这种辩法确实挺方便,但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它。
我们也可以把前两条原则合并为一条,因为人类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凭什么我们这个物种就该被特别对待?我无意在这里为这种区分辩护,但我对那些声称自己不认同这种区分、却又真能按自己的主张活下来的人,始终持保留态度。
[2] 孔子同样也是因为权力斗争失势而被逐出政坛。若不是这段漫长的被迫“赋闲”时光,他大概也不会在后世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