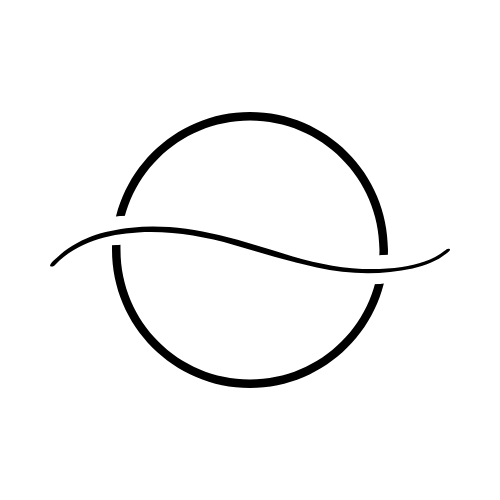识人,是一门艺术
What’s going on here, with this human?|By Graham Dunc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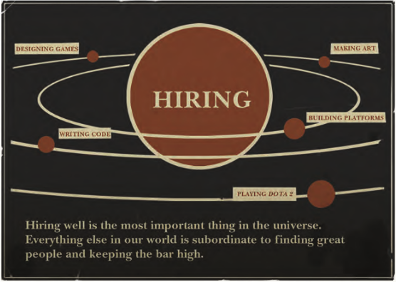
格雷厄姆·邓肯(Graham Duncan)是一位资深投资人,现任East Rock Capital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East Rock Capital是一家多家族投资办公室,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投资解决方案。在创立East Rock Capital之前,邓肯曾在其他两家投资公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他于199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邓肯对人类行为和认知有着浓厚的兴趣,热衷于探索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机制。他经常在个人博客上分享关于人才管理、投资策略和个人发展的见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融合了心理学、管理学和投资领域的知识,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写过一句话:“人生的挑战,与其说是弄清楚该怎么打好一场游戏,不如说是搞清楚你到底在玩哪一场游戏。”
而当我试图搞清楚自己在玩哪场游戏时,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5年里,我一直在玩一场“人际策略”的游戏——反复在尝试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篇文章里,我基于自己做过的数千次评估,加上对这个话题几乎有点痴迷的兴趣,总结出一些关于“如何挑选合适人选”的建议。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别人在评估一个潜在的雇员、商业伙伴,甚至是人生伴侣时,能够判断得更快、更准。文章里既有行动建议,也有背后思考的底层逻辑。最后我还会附上一些我对常见性格测评工具的看法,以及我最常用的一些面试和背调问题。
杰瑞·宋飞曾被问起“变老是什么感觉”时这样回答:“我觉得,如果你人生还算幸运,那变老其实是一件值得享受的事……年轻的时候你对周遭一切看不太清楚。年纪大了,你一走进房间,立刻就能看出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史蒂夫·乔布斯在人生晚期曾对沃尔特·艾萨克森说:“如果说我在苹果有一个精神上的搭档,那就是乔纳森·艾夫。我们俩一起构思大多数产品,然后再把其他人拉进来……他既能看到全局,也能关注产品最细微的细节。”可以说,乔布斯和艾夫经过14年每天的交流,彼此之间的了解程度是10分满分。
那么,当你刚开始了解一个人、评估他们是否适合你的团队时,你能接近这10分的程度吗?
刚开始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我的水平估计只有3分。但后来我做了数千次面试,也花了数千小时跟推荐人聊天,帮助招了上百号人——一开始是在大学毕业后和别人一起创办的一家研究公司,后来是在我管理大型资金投资时招分析师和投资人。现在,当状态对了、条件合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时能达到7分。
很多人,无论是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别的行业,都觉得这些事很烦,是在偏离团队核心使命。但我越来越认为,这其实是组建团队中最关键的技能。说到底,能否看懂人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企业能走多远。游戏公司 Valve 曾说过:“招对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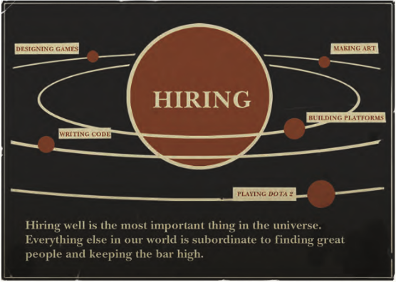
这个观点,其实是近年才兴起的。在工业时代的公司(比如美国钢铁公司、陶氏化学)里并不适用。但在像 SpaceX 这样高度复杂的智力型组织里,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再比如,二战时期的美军 vs 现在的海豹突击队:战场越复杂,选对人就越有杠杆效应。
UCLA 商学院战略教授理查德·鲁梅尔特的一个朋友,在读了大量商学院案例之后跟他说:“我觉得你每个案例,其实都只是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鲁梅尔特写道:“这是我以前从没人说出来的话,但一听就知道是对的。战略工作的大部分,其实都在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不是直接决定该干什么,而是先要搞懂现实的本质。”
所以,面试一个人的时候,不妨像鲁梅尔特那样,直接问自己一句:“我眼前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越是这么做,我越意识到,很多人以为招聘的难点——比如问出刁钻问题、定义岗位职责、评估技能——其实都没那么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更基础的任务:你到底能不能把一个人(包括你自己)看清楚?
把人看清楚(或者至少更清楚一点),不仅是为了找“最好”的人选,更是为了找最适合他们的位置。就算是在一群拥有高度职业选择权的人当中,我敢打赌,真正坐在“最能发挥自己才能、让自己有归属感”的岗位上的,可能也就20%。这对那80%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对他们的团队更是如此。
诗人戴维·怀特曾用“与现实的对话”来形容人生和职业的发展:
人所渴望的一切,从来不会按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到来……人生真正发生的,是你对世界的渴望,和世界对你的渴望,两者在某个前沿地带相遇。而那个前沿地带,是唯一真实的地方……你只能努力保持真实、脚踏实地,同时把眼睛和声音始终朝向你要去的远方,或是朝向你所遇之人的远方。
怀特的这段话,道出了招聘为何是一门艺术。当你能把一个人看清楚,你就能看到他与现实之间这场“对话”的全纪录,也能隐约看到他前方的地平线。有时你甚至能帮助他“听见”自己真正的声音,听见世界真正需要他做的事——那也许是你原本设想的岗位,也可能不是。
要想把人看清楚,有三件事需要学会:一是看到窗户中的自己;二是看到房间里的大象;三是看到我们所处的那片水。
第一部分:看到窗中的自己
在他的书《苏醒》(Waking Up)中,山姆·哈里斯用一个精彩的隐喻来描述“如何看穿我们看世界的框架”:
想象一下,你想让朋友理解,窗户其实也可以像镜子那样反射出人的影像。但偏偏,这位朋友从没见过这种现象,对你的说法充满怀疑。你带她来到屋里最大的一扇窗前——此刻的光线正好,反射效果非常清晰。但你的朋友一眼望出去,立刻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了:多美的风景!那是谁家的房子?那棵树是红杉还是道格拉斯冷杉?你开始试图解释,这扇窗其实有两个视角,她的倒影此刻就在她面前。但她完全没听进去——她只注意到邻居家的狗竟然跑出了前门,正沿着人行道飞奔而去。每一秒钟,你都清楚她正直勾勾地穿过自己的倒影看出去,却完全没有看到它。
如何让一个人意识到,这扇窗的某个角度其实也是镜子?正如哈里斯所说:这事其实很难。
但现实是:如果你无法先看清自己,你就无法看清别人。你们两人共同塑造了这一刻的互动。如果你说话时屏住了呼吸,也许会让对方不自觉地也屏气凝神,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紧张”。如果你的问题隐含着一种对竞争力的价值判断,对方的回答也可能不自觉地迎合了这个倾向,而在别的情境下这种一面可能完全不会出现。
我脑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三十岁那年做面试的样子:就像那个只顾望风景的朋友——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大脑正在不停地对面试者做出快速判断,仅凭一点点信息就开始构建故事:“这点我喜欢”、“那点我不喜欢”。他不断把自己的“现实”投射到对方身上,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哪怕是很资深的人,在正式面试的场合里也可能不是他们平时的样子。那是一种权力关系,他当时并没有足够重视。他还没意识到,虽然他能敏锐识别“忽悠”的能力是一种天赋,但这种能力也会形成盲区——导致他错过了一位优秀的销售,或一个虽然还在职业早期、偶尔会说些陈词滥调但本质很不错的人。
为了帮自己“看见窗中的倒影”,我试过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就是人格测评。这些年我大概做过三十多种不同的性格测试,就是为了更了解自己的优势与短板,也更清楚地看见别人。
像许多人一样,我最早接触的是迈尔斯-布里格斯(MBTI),我通常的测试结果是 INTP。但我也试过很多别的,比如“五大人格”模型(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ghSMART 的问题(比如:“我要是打电话问你前上司,他会在 1 到 100 分里给你多少分?”),还有前贝恩咨询顾问帕特里克·兰西奥尼提出的理想团队成员三要素:“谦逊、渴望、聪明”。也有一些更偏哲学的体系,比如鲍勃·凯根的成人发展阶段理论,以及九型人格(Enneagram)等,这些方法虽然更复杂、上手门槛更高,但也值得投入。 (在文章结尾,我会详细分享我对这些工具的使用体验。)我建议大家使用不止一种测评方式——这样你就不会被困在某一个框架中,看问题也更全面。
第二部分:看到房间里的大象
真正看清别人,其实是一种“调频”行为,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提出了一个很棒的隐喻:想象你正骑在一头巨象上,面试的那个人也骑着另一头巨象(据说海特是在一次迷幻药体验中想到这个“骑象人”比喻的)。在他的设想里,我们的“意识”是骑象人,而我们的潜意识动机就是大象——强大、固执,而且大多数时候,大象才是那个真正决定往哪儿走的。
关键在于:骑象人并不总是能看清自己骑的这头象。
所以,不如换个角度来看面试:其实房间里有两头大象,一头是你的,一头是对方的。坏消息是,你对这两头大象基本都看不清。好消息是,有很多其他“骑象人”曾经和那头象同行过。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观察、再加上其他人对这位候选人(和他的大象)的长期印象,再剥离掉你自己(以及他们)固有的一些偏见,就能大致拼凑出这个“人+大象”的组合真实的模样。
组织行为学家克里斯·阿吉里斯曾区分过“宣称的理论”(espoused theory)和“实际使用的理论”(theory in use):一个人在面试中说出来的,是他们的“宣称理论”;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依赖的,是另一套更深层、更自动化的“实际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说一套做一套”的区别,而是认知层面上的自我理解 vs 行为驱动机制之间的落差。面试中你是在和“骑象人”交流,但要知道,一到现实情境里,那些“宣称理论”往往会被大象的“实际理论”轻易取代。
有时候,一些问题可以让你稍微看见对方的大象。比如:“你对什么事有强迫症?”或者:“你有没有某个瞬间,被某位长辈做的某件事点燃了?当时你直觉觉得——‘他和我一样,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或者问:“如果让你配偶 / 兄弟姐妹 / 父母用十个形容词来描述你,他们会怎么说?”如果候选人有能力换位思考、并愿意诚实表达(大约50%的人能做到,年纪大的人比例更高),这些形容词往往能同时揭示出骑象人和那头象。
在面试中,我尽量营造一种“静”的氛围,以便区分信号与噪音、骑象人与大象。最简单的做法是:尽量少说话。还有一个办法是:鼓励对方来提问。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你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比你想象中要难——你要让对方觉得“问真实的问题”是安全的,同时你自己还要简明回答,不然时间会不够(尤其是他们问得很好时)。我会把每个问题记下来,有时还会反问:“我来回答,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想捕捉的,是那种“求知欲”的气息——它很难伪装。
我也会尽量卸下自己对岗位的预设,避免带着太多框架感去面试。我喜欢开场时问:“如果你是面试官,你会用什么标准来评估这个岗位?”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它的回答总是出人意料。有些人你以为会讲抽象,却给出具体操作;有些人反而帮你优化了原有的评估标准;有些人用的术语会暴露出他是在玩别人的游戏,而不是在自己设计人生剧本。无论哪种答案,都很有启发。
当然,你在面试中可能偶尔能“瞥见大象的影子”,但一定要记住:你大多数时候其实是“盲人摸象”。真正更高效的方式,是去找那些真正了解这头大象和那个骑象人组合的人——他们经历过这个组合在现实中的实际运作,而且最好是经过了很多次长时间的互动(比如配偶、兄弟姐妹、老同事)。
面对面试只是一个输入,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个。依赖我自己的直觉判断,有时结果还不错,但我也发现,要真正保持“我在一两个小时内能看清一个人”这件事的谦逊,比我一开始想象的要难很多。
有时候,在面试前我会重新读一段菲利普·罗斯的小说《美国牧歌》里的话:
你还不如去当一辆坦克的大脑。你在见面之前就把他们想错了;真正见了面,又理解错了;回家之后,试图向别人转述这次见面时——还是全错了。而且,对方对你的理解通常也一样糟糕。整个过程说到底,就是一场绚丽夺目的幻觉——本质上毫无感知力,一出关于误解的精彩闹剧。
现在,我认为“面对面参考人访谈”(和真正了解候选人的人深入聊)比面试本身有五倍的价值。如果你跟推荐人之间本身就是高度互信的关系,那这个访谈的价值甚至可能达到十倍——尤其是这个推荐人自己没有什么偏见、能真正看清候选人。
考虑到推荐访谈的重要性,也许你自己的面试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这些后续的“推荐人对话”打好基础——也就是说,把你对候选人的判断,仅作为“多个视角之一”来看。这需要你有能力“同时保留多个可能”,一种约翰·济慈称之为“负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状态:放下预设、不急于判断,像海绵一样吸收对方的现实,不急着把自我投射进去。某位作者把它定义为:“一种摆脱企图、专注观察的无辜;一种细水长流的好奇心;一种愿意等待、不急于得知真相的姿态,让人能够真正触碰到另一个世界的真实。”这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你亲自面试的那段体验是立体、生动、多感官的;而其他人的观点,往往只是冷冰冰的语言。
根据我的经验,真正做到“把你自己的判断和推荐人的判断并列”时,你心里应该是有点不安、甚至有点混乱的。如果你觉得完全顺畅、完全清楚,那你可能做错了。你应该偶尔对这个人感到困惑。如果你最先看到的是他的“短板”,你要意识到你还没发现他的“长板”;反过来也一样。
我在做推荐人访谈时,会特别留意那些“古怪而优秀的特质”。当我自己被别人打推荐电话时,经常会感觉到一种带着轻微敌意的“找茬”语气,比如:“乔治怎么干了两年就走了?”这种语气会让我关掉自己的信息输出。我自己打推荐电话时,会想象自己是整个对冲基金 / 私募行业的人才主管,对候选人没有立场,只是想帮他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带着这种心态,我对人更能容纳他们的不同,也更容易判断准确。
当你积累的推荐访谈样本够多时,你也会开始形成对“推荐人可信度”的判断——他们自己的样本有多大?他们有啥偏见?你也会慢慢学会辨认什么是那种“用拳头砸桌子般”的力荐。我还记得14年前为公司招 CFO 时做的一个推荐访谈:一位曾和他共事的女性,语气里透出一种“你怎么还在浪费时间问我,怎么不去拼命把他拉进来?”她甚至有点替我感到遗憾,觉得我还没意识到他有多好。从那之后,我一直在听这种语气——每当听到,都是高价值信号。
最难判断的是“沉默的狗”:如果推荐人熟知候选人,但没表现出那种情绪饱满的力荐,那这只是因为语境特殊(比如对方刚加完班、心情不好、吃了点醋),还是里面真的藏着什么信号?这个判断,得靠长期锤炼,慢慢建立你的“感应力”。
我也试着坚持一个默认假设:“每个人在某个地方,都是 A 级选手。”用这个视角去面试,一个人就不再是你要二选一地评判的对象,而是一个现场拼图、一个让人着迷的谜题——你要找出那头大象和骑象人最擅长做的事是什么。这也许就是你原本设计的岗位,也可能是别的某个完全不同的位置。
第三部分:看到那片水
2005年,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场如今已被广泛传颂的演讲。他开场讲了个小笑话:两条小鱼游着游着,遇到一条年长且睿智的大鱼。“嘿,小伙子们,水怎么样啊?”老鱼打招呼说。小鱼们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其中一条转头问另一条:“水是啥?”